
鄧安慶/文
一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TheMemoryPalaceofMatteoRicci)出版于1984年,那一年史景遷48歲。在此之前,他已經(jīng)出版了若干本書,都是著眼于明清。曹寅、康熙、洪秀全、湯若望……這些歷史上的真實人物都以鮮活的形象活躍于他的作品中。利瑪竇作為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最早傳教士之一,成為史景遷下一個研究和書寫的對象,自然順理成章。熟悉史景遷的讀者,應該都知道讀他的書從來不用擔心看不懂。他雖然是一個舉世聞名的歷史學者,可他的著作卻從不會像其他專業(yè)學者那般需要閱讀門檻,但這并不意味他的著作是淺薄的。閱讀這本書的感覺就像是看小說,順滑至極,如果不留心,你幾乎都意識不到每一句看似簡單的話背后都有相應的史料支撐,這就是一位史學家的功夫所在。他沒有把那個辛苦的前期工作呈現(xiàn)給你,他只給你端來一盤盤好吃的菜,你開心地吃下去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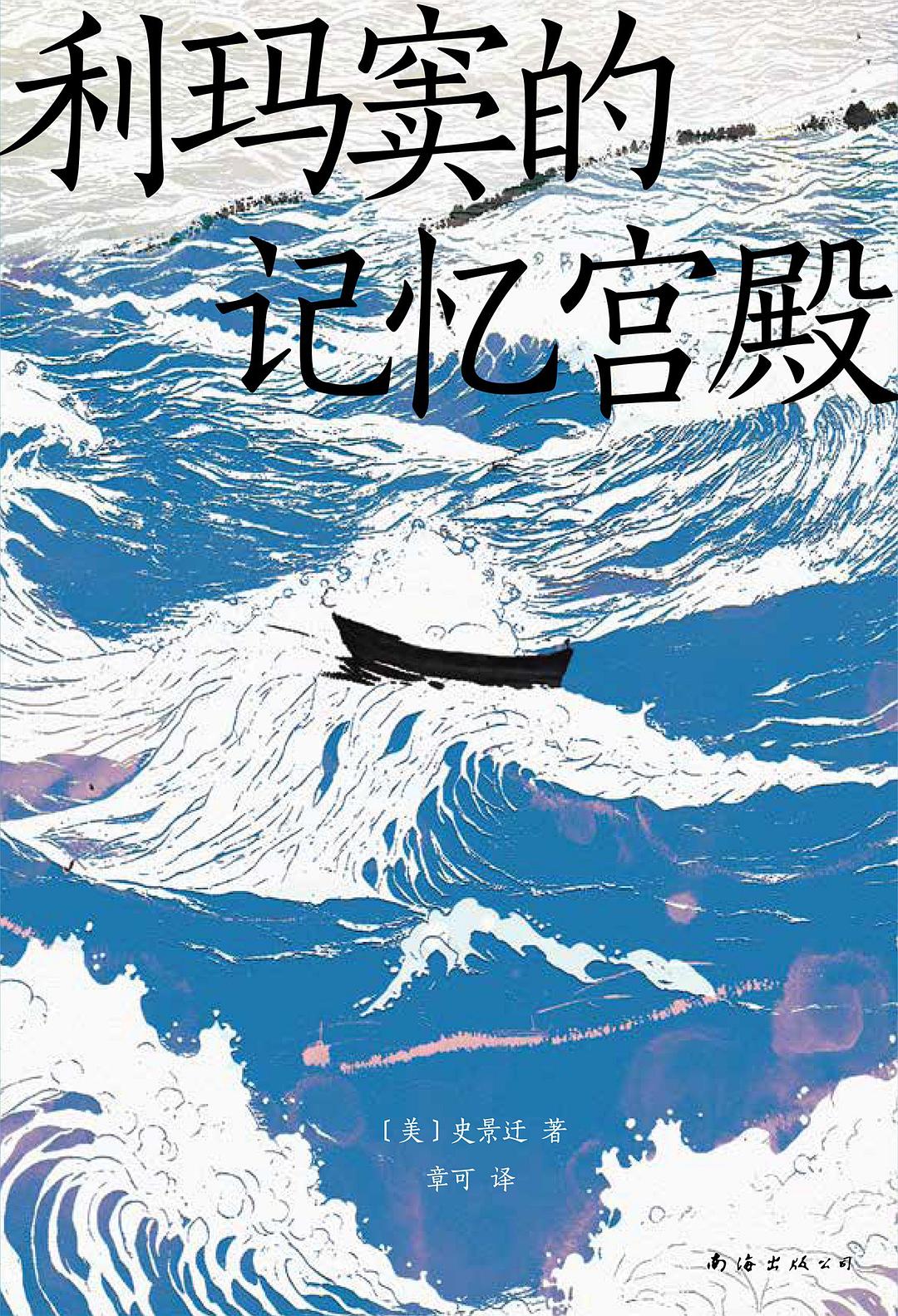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美] 史景遷 | 著
章可 | 譯
新經(jīng)典文化 | 南海出版公司
2024年8月
史景遷最為我們熟知的寫作手法就是“講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言,“故事就圍繞在你的周圍,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重新體驗歷史人物所經(jīng)歷的事情”。他以獨特的視角投向漫長的中國歷史,從中挖掘出或知名或無名的人物,搜羅爬梳大量可貴的珍稀資料,并有機地把這些資料放進歷史的文化內(nèi)涵中去審視、探究、剖析,最后呈現(xiàn)出的是一部部引人入勝的作品。費正清曾如此稱贊,“真切摹寫出人物的品性及其處境,史景遷親切地帶領我們走進這些人的生命,讓我們仿佛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仿佛跟他們有過直接的交流”。
具體到此書,史景遷沒有采用傳統(tǒng)的編年史寫法,而是從利瑪竇留下的8個記憶碎片——4個漢字(武、要、利、好)和4幅圣經(jīng)版畫,搭建起一座記憶宮殿。這座記憶宮殿,“為數(shù)不勝數(shù)的概念提供安置之所,正是這些概念構成了人類知識的總和”。每個人都可以根據(jù)自身的實際情況,搭建出獨屬于自己的記憶宮殿。史景遷在此書中,帶領我們闖入了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打破慣常的線性敘事,用片段化的“記憶”把利瑪竇和他的時代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其切入角度,可謂相當精妙。
二
在很多的歷史學著作里,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史實與史料,但我們很難看到“活人”。當然這些書中寫到了很多人的事跡,可是我們隔著久遠的時空,很難與他們產(chǎn)生共情。史景遷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這些人從塵封的歷史史料里“復活”,其難度在于如何去與人物“感同身受”,這需要作者深入到人物所生活的時代,充分地感知人物的處境(機遇、困境),更進一步地要深入到人物的內(nèi)心,甚至捕捉到人物的情感和情緒。
這樣做是有巨大風險的,尤其面對利瑪竇這樣的人物,關于他的史料不算少,可也沒有豐富到能取之不盡的程度。史景遷有時候必須站在既有史料的基礎上,往前跳躍一步,甚至多步,才能夠走到利瑪竇的內(nèi)心深處。到了那里,就離開了史學嚴格遵循“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的鐵律,邁入到文學創(chuàng)作的領域了。
多虧了史景遷的冒險,我們得以走進利瑪竇的人生現(xiàn)場。1582年(明萬歷十年),利瑪竇被派往中國傳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華傳教28年。在此期間,他向中國社會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地理學知識以及人文主義的觀點,開了晚明士大夫?qū)W習西學的風氣。他與徐光啟等人合譯的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前六卷),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原有的數(shù)學學習和研究的習慣,改變了中國數(shù)學發(fā)展的方向,是中國數(shù)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幾何學方面,還與徐光啟、李之藻等共同翻譯了《同文算指》《測量法義》《圜容較義》等。利瑪竇制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圖,先后被12次刻印……我們還可以繼續(xù)羅列他的成就,可是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為什么萬里迢迢來到中國傳教?在這28年時間里,他經(jīng)歷了什么?為什么這些中國的學者愿意與他合作?又有哪些人在反對他?……帶著這些疑問閱讀此書,都會得到相應的解答。
利瑪竇生于1552年,中國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歐洲則正處于“大航海時代”的興盛時期。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槍炮推動下,諸多古老帝國的大門都被蠻橫地砸開了。不過那時明朝還不像晚清那般任人宰割,與歐洲也只是遙遙相望,雙方的關系是對等的,交流說不上密切,可也不算是隔絕。
那時,一批傳教士乘坐海船,漂洋過海來到東方,從印度到中國再到日本,都有他們的蹤跡——利瑪竇就是其中一員。史景遷提醒道,“我們應該記住,在某種層面上,如果我們要把利瑪竇的事業(yè)置于天主教勢力主動對抗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中,將其視為十六世紀晚期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槍炮推動的‘歐洲擴張運動’的一部分才能讓它獲得意義,那么同時,我們還應該從一個更為古老的背景——那個由基督教神父和懂得魔法、煉金術、宇宙學和占星術的‘有智計之人’共同撫慰人類心靈的世界,來看待他的事業(yè)”。
利瑪竇來中國傳教,可以想見不是一帆風順的,甚至可以說困難重重。他在給阿桂委瓦會長的信中,述及自己在中國的艱難歷程時如此說道:“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里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兄弟的危險。”這完全不是夸張的修辭,而是極為殘酷的現(xiàn)實。
他一入中國,就陷入到“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中”,當他居住在廣東肇慶時,民眾對他和他的同事、隨從都好奇至極,“這些民眾日夜圍繞在他們的住宅四周,不時透過門縫窺探他們的一舉一動,有時只是出于好奇,更多時候則帶著嘲弄和敵意。對西方人以及那些中國皈依者們而言,選擇居于中國就意味著要習慣被人憎恨。無處不在的危險可能來源于國家之間的沖突,也可能由幾枚錢幣之類的小糾紛所引發(fā)”。身處其中,其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倘若想進一步傳教更是舉步維艱,“比起那種雙方全副武裝擺開架勢的決定性戰(zhàn)役,這場戰(zhàn)斗無疑更為孤獨和冗長。我們可以猜想,在這場持久的精神消耗戰(zhàn)中,利瑪竇的忍耐力已到了何種程度,因為有太多的中國人將他視為敵人”。
中國人總是對利瑪竇的滿頭白發(fā)表示驚訝,并奇怪為什么他年紀不大卻看起來如此蒼老。利瑪竇無奈地表示:“他們正是我白發(fā)蒼蒼的原因。”利瑪竇還說,上帝選中了他,賜予他12年含辛茹苦、飽受屈辱的生活。
在這樣的困境下,利瑪竇雖有抱怨,卻從未氣餒。他首先要攻克語言關。他從完全不會說漢語,到最后居然能用漢語寫作,語言天賦自不必說,所下的功夫也是驚人的。他依靠自己的方法,用了12年時間學會漢語,“從他存留下的書信中,我們能夠推測出他那艱辛的學習歷程中最重要的幾步。1583年,利瑪竇獲得中國官員允準,在肇慶城中安定下來,到了第二年的夏秋時節(jié),他已經(jīng)開始講道,并偶爾會聽人懺悔。在1584年10月,他嘗試不帶翻譯,自己與人對話,并自感已有很好的漢語讀寫能力;到1585年11月,他已經(jīng)可以在人群中流利地演說,而且在中國助手的協(xié)助下幾乎能閱讀所有看到的東西……在1593年12月,他和人宣告要開始一項攻讀‘四書’的計劃……利瑪竇還試著要把‘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到1594年10月,在連續(xù)10個月每天上兩堂長課之后,他終于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我已經(jīng)鼓起了足夠的勇氣,從現(xiàn)在開始我可以自己用中文寫作了。’”
利瑪竇學會漢語的關鍵,書名就做了提示:“記憶宮殿”。這是一種嚴格的記憶法,利瑪竇就是用這種方法攻克了語言關,并以此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利瑪竇發(fā)現(xiàn)對于那些雄心勃勃意在攀登科考階梯以獲得功名仕宦的中國年輕人而言,牢記那些經(jīng)典作品至關重要。利瑪竇聰明地利用那些中國朋友對熟記詩書的渴望來宣傳自己的記憶學說,其目的是想引起中國人對他的文化的興趣,進而引導他們對上帝產(chǎn)生興趣。
利瑪竇不僅在學習語言上取得如此大的成績,“在中國的那些時光里,利瑪竇基本上對所有的學問分支都有所涉獵,包括鐘表制造、光學、天文觀測、測量、音樂、地理學、幾何學。憑借他對學院里獲得知識的記憶,加之隨身攜帶的為數(shù)不多的書籍,便足以應付大部分領域了”。前文中列舉的那些成就,足以說明這套記憶法的厲害,也可見利瑪竇之博學多識。
三
利瑪竇所做這一切,主要目的是讓更多中國人關注他的科學成就,從而使他們更容易接受基督信仰,“在十六世紀90年代后期,利瑪竇找到了一套勸人皈依的辦法,那就是發(fā)展私人關系和傳播科學知識雙管齊下。當然,利瑪竇希望通過討論嚴肅的科學問題來吸引優(yōu)秀的中國學者入教,這一做法被證明是有效的”。瞿汝夔、徐光啟、李之藻等中國精英知識分子,都是被利瑪竇以這種方式感召入教。
為了讓福音能夠傳播,利瑪竇可謂想盡了一切辦法,他身懷的技能、巧計、訓練和記憶所能提供的林林總總的方法都用上了,“棱鏡、鐘表、畫像、歐幾里得幾何、傳教文書、晚宴、教會神父、古希臘羅馬哲學家,所以的這一切,都在圣母的神圣指引下一一展現(xiàn)”。有人皈依,自然有人反對。利瑪竇在中國長期生活,也逐漸接觸和了解儒釋道對中國士人的深遠影響力。他也不可避免地會與中國本土的宗教人士發(fā)生沖突。比如在1599年,他在南京城的一次宴席上,與三淮和尚就宗教問題展開辯論。兩人相互吼叫,爭論過程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利瑪竇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傳教生涯呢?或許從他的一段自白里可以窺見一二:“生活在后世的人們,往往無法了解前時代的偉大事業(yè)或行動如何起源。我時常揣思,這是緣于何故,發(fā)現(xiàn)只能如此解釋:一切事情(包括那些最后取得極大成功的)在肇始之初,是那樣微弱渺小,人們自己都無法說服自己相信,它將來能成就如此宏大之局面。”他沒有見到中國的皇帝,自然也沒有辦法去感召皇帝皈依,這是他始終無法釋懷的遺憾。但站在今人的角度看,他能在陌生的帝國,以驚人的意志力拓展出一片小小的空間,讓他的信仰之種落地生根,且影響深遠,這樣的成就少有人能及。
1608年年初,他的《畸人十篇》出版。在書中利瑪竇將自己定義為一個“畸人”(“矛盾的人”)。到了秋冬,他開始撰寫《中國札記》,給后人留下了詳實的記錄。1609年,第一個圣母會在北京城成立,走到這一步,耗費了利瑪竇畢生的心血。
遙想當年,他從里斯本到印度果阿,航行長達6個月,需要兩次穿越赤道,期間遭遇了各種艱難,而后要從澳門進入廣東肇慶,又等了一年之久。此后的28年,他費盡心思嘗試打開中國人的內(nèi)心世界。史景遷有一句話讓人分外動容:“在這片未知的地域,利瑪竇已經(jīng)走得太遠,遠超他預料。他有時茫然無著,不知自己是否應該返回,自己是否還能返回。”
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在北京去世。終其一生,他再也沒有回到故國。也許在他的國家,少有人會提起他的名字。但在中國,他在歐洲與中國之間鋪就了一條真實可行的交流之路,讓兩大文明對接碰撞,其功勞值得銘記至今。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